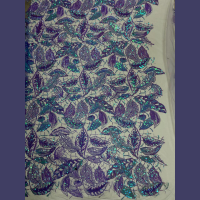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5日發布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該期報告的主題為“全球制造業下行與貿易壁壘上升”,凸顯了當前全球經濟陷入同步放緩境地的原因。將2019年世界經濟增速下調至3%,這是自2008—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相比2017年全球同步回升時期3.8%的增長率也是一次嚴重的倒退。
全球經濟同步放緩 未來回調難以預料
IMF下調了全球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2019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相比7月上期報告,IMF下調美國0.2個百分點至2.4%,下調歐元區0.1個百分點至1.2%,下調英國0.1個百分點至1.2%,日本維持0.9%的低增長預期。同時,IMF下調中國0.1個百分點至6.1%,大幅下調印度0.9個百分點至6.1%,包括東南亞、拉丁美洲和中東等地區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速也都被不同程度地下調。IMF將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原因歸結為貿易壁壘不斷上升,貿易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升高導致的資本貨物投資和需求的雙雙下降,以及汽車等制造業行業面臨特殊沖擊而呈現的收縮下滑。更重要的是,2019年的增長表現還是在全球寬松貨幣政策以及中美兩國積極財政政策共同作用下取得的,并且服務部門在消費和就業方面發揮了穩定器的功能。
IMF雖然也下調了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0.1個百分點,但3.4%的增長預期仍高于2019年的3%,顯示了對2020年全球經濟回調的信心。IMF預期2020年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率仍將保持1.7%,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率則有望從2019年的3.9%回升至4.6%,且認為回升大約一半的原因在于土耳其、阿根廷和伊朗等承壓國的復蘇或衰退程度的緩解,其余的原因在于巴西、墨西哥、印度、俄羅斯和沙特等2019年增速大幅放緩國家的復蘇。然而,事實上,全球經濟能否在2020年實現回調充滿不確定性。一是IMF對美國、中國和日本三大經濟體2020年的增速預期比2019年分別低0.3、0.3和0.4個百分點,這可能會導致全球市場需求和資金供給的不足,高度依賴全球市場需求和投資的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回調就缺乏基礎條件。二是土耳其、伊朗和沙特等國都正處中東地緣政治沖突的中心地帶,伊核問題、土耳其與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沖突等造成地區緊張局勢的問題很難在未來1年時間里得到妥善解決,甚至還可能出現新的“黑天鵝”事件攪局,都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復蘇充滿極大的不確定性。此外,隨著2019年全球寬松貨幣政策的普遍施行,2020年很多國家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越來越小,且財政貨幣政策面臨金融脆弱性風險的不斷增加,更進一步增添了其刺激2020年經濟回調的難度。
結構性問題是根源 中國經濟展現定力
IMF的報告將愈演愈烈的全球貿易爭端視作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最重要原因,給予了高度關注,并呼吁各國應當果斷制定各項政策以緩解貿易緊張局勢、重振多邊合作,及時為經濟活動提供必要的支持。然而,不斷升級的全球貿易爭端可能只是導致全球經濟放緩的表面原因,導致貿易摩擦產生的一系列結構性問題才是根本性的挑戰。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出現明顯分化,在經濟和貿易總體規模上逐步趨近結構性平衡。這一方面動搖了發達國家在全球經貿規則制定上的主導地位,引發其對抗心態;另一方面增強了發展中國家的談判基礎和談判能力,使發展中國家更有底氣和愿望真正參與到全球經貿規則的制定中。多年來,雙方圍繞發展中國家特殊與差別待遇、非市場經濟主體行為以及知識產權、數字貿易、農產品補貼等新老議題展開討論,但多哈回合談判卻幾乎沒能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美國轉而采取單邊措施,以加征關稅為手段,在區域和雙邊層面施壓貿易伙伴接受美國的新貿易規則,并以此脅迫各方,意欲重掌多邊貿易規則的制定權。但美國此舉遭到了中國、歐盟、印度等多方的強烈反對。因此,世界經濟格局的結構性變化引致的多邊主義危機是當前全球貿易爭端的根源,短期內重啟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困難重重。
美歐等發達經濟體自身也面臨嚴重的國內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使其在經濟增長乏力的同時逐步走上貿易保護主義的道路。發達國家作為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從中獲益良多。但其國內收入分配存在的問題導致全球化帶給發達國家的收益高度集中于財富金字塔頂端的精英階層,而人數眾多處于社會中下層的普通民眾的相對經濟地位不斷下降,淪為經濟全球化的失意者。在部分政客和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西方國家中下層民眾將自己的失意歸罪于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成為現階段反全球化的主力軍,民粹主義甚囂塵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將貿易保護主義作為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以迎合民粹。美國對中國、歐盟等發起的貿易爭端已對全球價值鏈和國際貿易的運轉產生了巨大的破壞和風險,降低了各國制造業投資和消費需求,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回暖的最大障礙。2019年美國經濟增速放緩、長短期國債利率倒掛、貨幣政策轉入降息周期等都預示著2020年的美國經濟充滿不確定性。特別是美國此輪經濟擴張已創歷史最長紀錄,新一輪衰退來臨的周期性魔咒很可能不久就再次響起。英國脫歐問題也始于相似原因,未能共享一體化收益的中下層英國民眾通過公投使英國走上了超過三年、至今仍懸而未決的脫歐之路,給英歐雙方的貿易和投資造成極大不確定性,阻礙英歐經濟的增長。
除階層的結構性差異外,發達經濟體國內地區間也存在結構性差異。IMF報告就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發達經濟體內部的地區差異有所加劇,反映出部分地區通過經濟集中度獲益,而其他地區則出現相對停滯的情況。落后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更低,工農業就業的比重更高,且不利沖擊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持續時間更長、調整更慢。美國等發達國家對落后地區采取的針對性政策還需長期的精細校準,才能有效發揮促進作用。
中國2019年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速下降到6.0%,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但必須認識到這一增速是中國在面臨國內外諸多風險挑戰的復雜局面下取得的,而且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仍保持著最高的增速,充分展現了中國經濟的韌勁和定力,并且中國仍有足夠的政策空間和市場空間保持經濟的平穩運行。中國經濟雖然也面臨著一系列結構性調整的挑戰,但我們正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逐步實現經濟增長從要素數量擴張驅動向創新驅動發展的轉型,從主要靠投資和外貿拉動向更多依靠國內消費拉動的轉型,從價值鏈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級的轉型。在保持經濟增長和就業穩定的情況下,還要確保金融穩定性。中國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可能影響短期的經濟增速,但其解決將有利于長期的經濟質量。中國還將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深度和廣度,為全球經濟的恢復和增長提供動力。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消息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