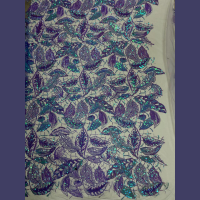日本內閣府3月7日公布了1月景氣動向指數初值(2015年為100),其中一致指數為97.9,環比下降2.7點,連續3個月惡化;先行指數為95.9,環比下跌1.3點,連續5個月惡化。
景氣動向指數來源于企業調查,根據企業家對企業經營情況及宏觀經濟狀況的判斷和預期編制,由此反映企業生產經營、經濟運行以及未來經濟發展狀況。日本的景氣動向指數根據工礦業生產等7項經濟指標綜合計算得出。其中,一致指數反映景氣當前狀況,先行指數反映數月后景氣動向。
根據此次數據結果,日本內閣府將總體經濟形勢評估由“停滯”下調為“勢頭變為下行”。日本經濟真的要開始衰退了嗎?其經濟真實運行現狀和趨勢如何值得關注。
“安倍經濟學”透支了未來政策空間
2012年底安倍上臺后推出“安倍經濟學”,由“大膽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三支箭構成,政策實施至今已6年有余,日本經濟也出現了新的變化。
一方面,迎來戰后最長經濟擴張期。日本政府在2019年1月份月度經濟報告中表示經濟“正在溫和復蘇”,事實上宣布了日本經濟擴張期達到戰后最長的74個月,而這也確實部分歸功于“安倍經濟學”。其大規模量化寬松釋放了大量流動性,誘導日元貶值,貶值幅度一度高達50%,由此帶動企業出口增加,利潤大幅上漲,日經股指上揚至20000點以上。另外配合政府積極財政投資,日本GDP較安倍上臺之初增長近60萬億日元(100日元約合6.03元人民幣),這是安倍引以為豪的成績單。
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潛在動力不足,結構改革遲緩。日本經濟擴張的同時也應看到其增速低、動力不足的一面。此次擴張期GDP平均增速僅為1.2%左右,遠低于戰后高速增長期“伊奘諾景氣”的11.5%,屬于低水平增長。據日本央行測算,未來5到10年日本經濟潛在增長率僅為1%左右,表明經濟增長后勁不足,加之人口少子老齡化趨勢不減,將導致經濟擴張難以為繼。日本設置了2%的通脹目標,但一再推遲達成時間,側面反映了占GDP60%左右的消費持續低迷,難以增長。目前日本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三分之二左右,在發達國家中基本處于最低水平,這與其經濟結構改革遲緩密切相關。
此外,“安倍經濟學”過分透支了未來政策空間,致使風險不斷累積,若再次發生大規模經濟危機,日本政府或“無計可施”。根據IMF統計,日本國家債務占GDP240%左右,是發達國家中最高水平。而由于日本央行不斷購買國債等,致使其資產負債表膨脹,日本已成為G7中首個央行資產超GDP的國家。大量的國債購買扭曲市場,加之負利率的實行,日本商業銀行正遭受史上最難經營期。現在日本貨幣政策空間被壓縮至極限,回歸正常政策的難度也不斷增加。
為救經濟日本政府打算長期布局
對于日本經濟本身的結構性問題,政府心知肚明,對此也制定了一系列經濟增長戰略,重點而言日本今后或將在以下三方面發力:
一是搶占產業技術革新潮頭。安倍政府明白存量改革難以取得成效,故從增量方面入手,推出“第四次產業革命”新理念,希望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的開發及運用,構建新產業體系,帶動日本整體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近日表示,日本在創新能力方面沒有得到充分認可,今后將在全球創新中發揮主導作用。
二是擴大勞動力來源,發展養老醫療教育等優勢產業。隨著少子老齡化發展,日本勞動力人口不斷減少,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相關政策,包括鼓勵生育、延遲退休、增加女性就業崗位和吸引外國勞動人口等。這樣的社會結構也倒逼日本在養老醫療教育等方面投入更多,制定更好的社會保障措施。日本政府積極推進教育無償化和幼兒看護保障,利用ips細胞精準醫療等最新技術領域也有所突破,在未來全球進入老齡化社會的趨勢下,日本或許在準備工作上將走在前列。
三是充分拓展外部市場空間。日本國內市場資源空間有限,要想長遠發展必須借助國際市場,這也是日本貿易和投資立國的根本原因。日本將大力倡導自由投資和貿易,不斷擴大海外市場版圖。2018年日本企業海外并購總額近30萬億日元,創19年來新高。另外除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日歐EPA等大型自貿協定,日本還與多國簽署了雙邊EPA協定,不斷提高自由貿易比例。
綜上,中短期內,日本仍將于低位增長徘徊,甚至不排除暫時衰退可能,但其長期布局不容忽視。
(顏澤洋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
消息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