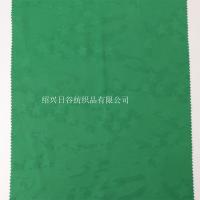有人說,旗袍是女人的第二層皮膚,再沒有哪一種服飾比它更能展示女人的身體曲線和審美品位。的確,在那一塊塊或華麗或樸素的面料背后,一對精心制作的扣子,一個恰到好處的點綴,一針一線針腳細密勻稱的手工,凝結(jié)的是舊時手藝人的畢生所學,它美,美在匠心獨具的設(shè)計,美在嚴謹考究的做工。
而今,旗袍輝煌不再,我們也只能從舊照片或影視劇中回顧它曾經(jīng)的風光。但總歸有人不甘心這份獨特的美麗被滾滾紅塵所堙沒,重操舊業(yè),傾其所有,只為尋回丟失已久的“初心”。
還原民國時期的美麗
2012年,張濟鏻經(jīng)人介紹,到一家旗袍店擔任經(jīng)理。短短一個月內(nèi),他看到無數(shù)女性顧客因為旗袍而兩眼放光。“那是一種很難用言語去形容的神采,我覺得旗袍對她們來說,是魂牽夢繞的品類,將來的市場應該很廣闊。”
張濟鏻是學美術(shù)出身,對自己的審美很有自信,加上他曾經(jīng)在日本工作過幾年,學過生產(chǎn)管理和技術(shù)管理,回國后從事的又是服裝設(shè)計與制作,看到市場上還沒有成熟的旗袍品牌出現(xiàn),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商機。出于對旗袍的熱愛和傳承傳統(tǒng)工藝的信念,他創(chuàng)辦了金鳳鑾旗袍設(shè)計工作室。
創(chuàng)業(yè)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張濟鏻的性格又是極其嚴謹,極其認真,為了學習旗袍的制作過程,他研讀了不少關(guān)于旗袍的著作,拜訪了很多做旗袍的老師傅,還購買了民國時期的旗袍進行研究。在拆解的過程中,張濟鏻一次次嘆服于老一輩從業(yè)者的工作態(tài)度,一件件保存了至少半個世紀的旗袍,質(zhì)量卻絲毫沒受影響,做工更是精致細密。
“比如旗袍有的部位是用糨糊粘上的,當我撕開那些部位時,那種刺啦刺啦的聲響震動著我的心。以前的糨糊都是自己做,要用溫度合適的水一遍遍燙,直到把糨糊熬出筋道。我甚至能想象,一位老藝人花了一上午的時間,只為了熬制糨糊,以確保做的衣服多年后不會因為他的疏忽而出現(xiàn)質(zhì)量問題。哪怕是一個小小的心形盤扣,也是用六個特別小的棉球做成的,不像現(xiàn)在有些制作者,只是隨意搓兩個湊合一下。”張濟鏻不確定自己做的旗袍能不能達到這樣的工藝標準,但至少,這種丟失了許久的手藝人的本分是他想要恪守的。“我既然做了旗袍,就應該做到能傳承、能把握的最好狀態(tài),不管要花多少時間研磨技術(shù)。”為了做好一個扣子,他能夠反復嘗試幾十遍、上百遍,以期最大程度地還原旗袍工藝。但他又不僅僅是在重復老一輩的工作,而是將自己所學到的先進技術(shù)融合進去,將以前一些需要靠經(jīng)驗把握的步驟進行量化,還申報了好幾項技術(shù)專利。“比如我申報的人體立裁專利,是將胚套在人的身上,直接進行裁剪,這種方式能最直觀地體現(xiàn)出人體的差異。還有手持三維掃描技術(shù),掃描完以后可以用3D打印出和客人人體結(jié)構(gòu)一樣的模型,這樣客人就不用來店里,只要在打印出來的框架上做立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