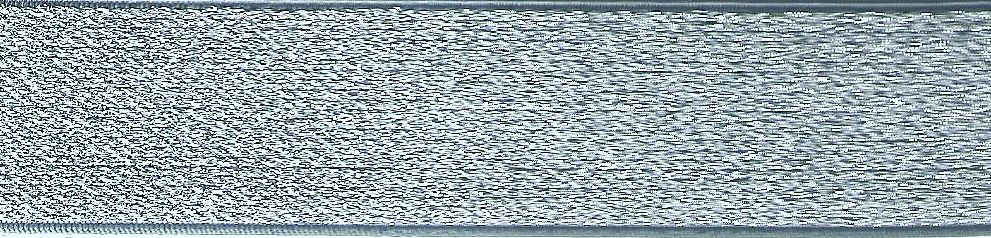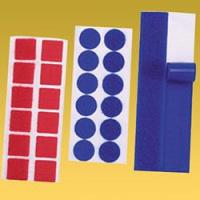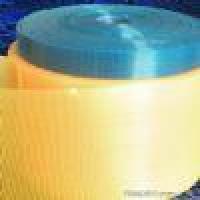一針一線,繡的是技藝、是感情,甚至是一個國家的靈魂,你能從人們端詳作品的眼神中讀出這種震撼力。
再次見到高勇是在甘熙故居里的工作室。跨過一道道門檻來到這不大的空間,著實被眼前琳瑯五色的手工制品驚艷到。后方的工作臺上,一盞亮著的小臺燈,燈下聚攏著針線、紙筆、剪刀、棉花、收納盒、風(fēng)扇等物件,鋪了一桌。還有一幅未完成的繡片,牧童吹笛放羊的圖案已基本成形,借著燈光泛出繡線特有的溫潤感。
這場景似曾相識,忽然就想到了在創(chuàng)意南京·最浦口文集匯上的他,靜靜坐在展位上縫制,耐心回答每個關(guān)于民俗的問題,哪怕對方并沒有要買的意思。
頂著南京市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人、秦淮區(qū)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理事等頭銜,高勇依然平易謙遜。于是,隆冬的上午,兩個板凳間,微漾起一個年近40的男人與傳統(tǒng)女紅的故事。
男兒做女紅,家傳手藝弘揚南京
在安徽蚌埠,高勇家的布藝是遠近聞名的。外婆的龍鳳香包、母親的虎頭棉靴,還有五毒肚兜、手工枕、繡花鞋等,都是人向往之的家傳禮物。依循祖制,繡花手藝傳女不傳男,可偏偏高勇一輩皆為男兒身。出于天賦與愛好,排行老二的高勇主動沿傳起母親的手工,雖歷經(jīng)波折,卻不曾輕言放棄,這一晃,已是17年的光景。
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手工的商機
高勇是看著形色不一的繡針、花樣長大的,外婆臨燈織縫的樣子他永遠不會忘記,潛移默化中,高勇從小就對裝飾、色彩多了一份敏感。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同鄉(xiāng)人大多選擇出門闖蕩,而幾分之差落榜高考的高勇也放棄了復(fù)讀的機會,順著打工潮來到南京。
“最初在一家外貿(mào)公司從事服裝設(shè)計。每年春節(jié)過后,同事們都會帶些家鄉(xiāng)特產(chǎn)到單位分享,當時我自己還沒什么手工作品,就把家中母親做的荷包、繡片等拿來了。也是機緣巧合,這些小玩意被前來洽談的外國生意人看中,他們興致勃勃地找到我,表達了將其推向市場的愿望。”高勇說,這件事給了他很大觸動。“印象中,家里手工制品都是逢年過節(jié)表心意的贈品,不曾涉及買賣,聽了他們的建議,突然就察覺到,原來這些司空見慣的物件本身竟有著如此大的商品價值。”那一次,高勇按照外國人的估價,收了一半的錢,完成了手工而來的第一筆生意。
輾轉(zhuǎn)多日后,高勇做了一個決定—辭職回家,潛心鉆研手工。“這可謂我人生一個重要轉(zhuǎn)折點。”那時候,他不到20歲。
堅守祖輩的文化遺產(chǎn)
在家跟母親學(xué)做女紅的日子里,高勇系統(tǒng)地接觸到各種花樣、鞋樣、構(gòu)圖、繪彩,包括給母親打下手、搜集整理民俗材料等,日復(fù)一日,耗費了很多心思,回報卻少得可憐。由于年少不夠耐性,高勇曾再次出走打工,可沒多久便折返家中。出于對手工的念念不忘,他對自己說,一定要把這事做好。
真正讓高勇決心扎根女紅行當?shù)氖峭馄诺倪^世。“外婆做了一輩子手工,那或許不是一個好的時代,沒有政府補助,沒有非遺榮譽,她都能堅持下來。而我趕上了傳統(tǒng)文化復(fù)興的時候,即便不是女兒身,也有義務(wù)將祖輩的技藝延續(xù)下去,至少對得起她們曾經(jīng)的守望。”高勇說,這個信念支撐著他走過最困難的時候。
成為南京布藝非遺傳人
高勇還記得,最初帶著手工藝品來南京時,父親只給了他85塊錢,自此,他一步步創(chuàng)業(yè),從擺地攤到做夜市、從跑教學(xué)活動到擁有了自己的工作室,百般滋味,冷暖自知。
對于南京這座城市,高勇很有感情,他說這里的包容性給予了他很多磨煉的機會。他一手創(chuàng)立的品牌“六朝手工坊”開始有了影響力,他自己也最終成為南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布藝)的代表性傳人。
“我始終相信,純手工的東西有文化、有感情、有一代代的守護與傳承,這是機器生產(chǎn)線永遠替代不了的。可手藝人只有養(yǎng)活自己,才能養(yǎng)活藝術(shù),有了生存才能談發(fā)展,有了發(fā)展才能談長存。從這個角度看,機器轟鳴、商品泛濫、價格低賤,這樣的現(xiàn)狀逼著手工藝人去做小生意,是一件多么無奈的事情。”
民俗文化需要更多關(guān)注
不以價格論價值,不以速度求學(xué)習(xí),這是高勇所希望的人們對待傳統(tǒng)手藝的態(tài)度。在跟隨文化部門出席世界城市論壇、大型民俗文化活動,以及走訪11國的過程中,外國孩子表達出的尊重給他留下很深印象。有一個細節(jié),當幾個孩子小心翼翼地問他:“我可以拿起這個看看嗎?”簡單的一句話,竟讓高勇感動不已。
憑借高超的針繡技藝,高勇近年來作為南京民俗文化的代表走訪了德國、波蘭、加拿大等11個國家,或是在當?shù)厮囆g(shù)學(xué)院做教學(xué),或是參加文化周交流活動。令他感觸頗深的,是外國孩子對世界文化無差別的尊重。
“舉個例子,同樣是手工展,不少中國孩子就直接拿起來擺弄,看完便隨手丟在一旁;而在國外,我卻屢屢遇到,幾個孩子好奇地打量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問我:‘可以拿起這個看看嗎?’僅一句話就讓人很感動。”高勇還提到,在教波蘭凱爾采市教學(xué)時,那里的孩子做起手工來很執(zhí)著,即使作品不完美,也能堅持完成,這一點很值得夏令營里某些半途而廢的學(xué)生學(xué)習(xí)。
“跑了這么多國家,在他國人文環(huán)境的感染下,我更愛自己的祖國,因為我們所受到的禮遇與尊重,無關(guān)金錢,完全是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在閃耀,你能從人們端詳作品的眼神中讀出這種震撼。”
呼吁第三方平臺做營銷
2013年,高勇創(chuàng)辦布藝品牌“六朝手工坊”,旗下三大品類:民俗裝飾、童趣物品與箱包掛件,其中,虎頭帽、虎頭鞋等最富民俗特色,而第三類產(chǎn)品如毛衣鏈、手機掛件、書簽、ipad套等都是后來自己琢磨出的,既實用又好看。除了甘熙故居里的實體店,六朝工藝坊還將銷售搬上了微店,微信生意絡(luò)繹不絕。
自制產(chǎn)品、自創(chuàng)品牌、自負盈虧,雖然六朝手工坊的生意上了軌道,但高勇并不認為這是傳統(tǒng)手藝最好的運營方式。
“或許我設(shè)想的有些理想化了。”他覺得,手藝人應(yīng)當與市場“脫節(jié)”一點,這并非指手藝人要養(yǎng)成不食人間煙火的姿態(tài),而是希望能有一個純粹的環(huán)境讓他們?nèi)プ鲎钌瞄L的事,不要在趕工之余還總顧念著產(chǎn)品怎樣包裝、去哪宣傳、銷售如何等一系列后續(xù)問題。高勇說,這些年為了品牌經(jīng)營,他各地跑活動、各校做演講、各方對接資源,分散了許多本應(yīng)投在創(chuàng)作上的精力。
高勇建議,如果能在政府的幫助下找到第三方平臺介入,幫助他們做營銷,讓專業(yè)的人做專業(yè)的事,情況會好很多。“但愿有一天,我能在早起時,想到的是作品還有哪些完善之處,而不是要到哪里參加繁瑣的商業(yè)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