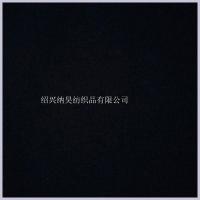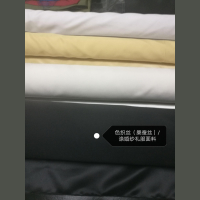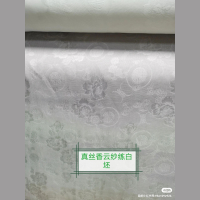別總想著優衣庫了!只不過是一個惡搞。帶你們看看面料,他不只是一塊布!
1、從腠理到骨髓
服裝設計是一門絕對光鮮的學科,但很少有人關注到光怪陸離的時尚背后為服裝設計提供血液的堅實壁壘:面料設計。也許相較服裝整體,面料的面貌在一段時間內都僅呈現出微觀的改變,而這種改變不足以對設計師和觀眾產生戲劇化的吸引,也不足以造就時尚的諸多社會化學反應,使得面料的創新在很長時間內并不受關注。但關于面料設計這個獨立學科的“事實”卻遠非如此。
其實早在18世紀,面料設計就已經開始以事實姿態引領時尚潮流。據統計,服裝風格的改變相對緩慢,但面料每六個月就會出現一次革新。成為一種垂簾聽政的藝術,“可能是因為紡織品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一部分,消費者往往對面料設計一無所知。”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紡織品專業主管,老牌的面料專家克萊爾·約翰斯頓(Clare Johnston)曾經這么說。“但對我們設計師而言,我們和面料一同成長,熟知它的歷史與沿革。盡管面料開發只是為了實現某種功用,但設計師與面料間已經培養起了某種默契。”
傳統的面料設計中,從基本原理歸納一般有這幾種常用方法:改變材料的結構特征,在既成品的表面添加相同或不同的材料,零散材料的整合設計,以及對原有材料的形態特征進行變形等。但無論那種都停留在較為表面的改造上。
面料設計行走到今天,其實已如信息技術一樣飛速更新迭代。當迪奧前面料設計師亞當·瓊斯 (Adam Jones) 與意大利頂尖紗線制造商Lineapiu合作,在開司米面料中織進24K金絲和4%碳纖維打造出了號稱“封印了30位專業心靈療愈師能力”的“輕紗”系列時,設計者甚至聲稱:只要穿著者注入意念,摩擦雙手,再放在胸前,為針織衫充電,它就可以按需要改變穿著者的情緒。無論這聽起來多么玄幻,曾經作為最容易出視覺效果的部分的面料設計,顯然已經走向了更復雜的未來。
織造的方式、印染的紋樣早已不是面料設計巋然不動的核心課題,有野心的設計師早已不想看著那些浮華卻始終無力的面料設計在平面的世界里做困獸斗。而三宅一生利用日本宣紙、白棉布、針織棉布、亞麻等材料創造出的各種浮出二維世界的肌理,對面料的實驗則標志著一種驅動力的顛覆:掰開、揉碎、重組、突變,有“百料魔術師”之稱的三宅一生對面料實驗這一過程的要求近乎苛刻,為了達到一種構造視覺上的滿意度,上百次的加工和改進司空見慣。這種內在和結構驅動的面料實驗一度驚艷所有設計領域。
2、學文學的前國腳設計師,馬蒂賈·科普
與三宅一生有著某種驚人視覺相似點的克羅地亞時裝面料設計師馬蒂賈·科普 (Matija Cop) 就讀的是薩格勒布大學面料設計系 (Fashion design of the Faculty of Textile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Zagreb) ,但他在進入時裝行業之前卻是一位田徑國腳以及一名克羅地亞語言文學類學生。這幾種跨越了人類智能最遙遠距離的身份顯然給他帶來了很不一樣的思維方式。
馬蒂賈的服裝架構看上去很像繁復的折紙,這種結構和質感是采用特殊的材料用激光切割成小塊,用“插羽”技術組裝在一起的結果,這樣做出來的作品在基因上很有如雕塑般的體積空間感,原始靈感來源于建筑和鑿石材料。談到面料設計,很多人都大談技術。但馬蒂賈·科普幾乎只字不提。在他眼里,為什么這么做比怎么做重要得多。馬蒂賈的創作方法很特別,他總是根據每個項目的性質和自己的目標,用概念性方法和動手的直觀方法各試一遍。他很少直接關注自己的設計有什么直接的形態效果或創造性顛覆,卻十分關注設計以及時裝制造行業在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里扮演的角色。“高級時裝是一種特定的時尚理念,每一個時裝秀只是各自重新將它闡釋一遍而已。”馬蒂賈覺得時裝的改變僅僅是人類社會改變的一個映射—社會變得快,時裝便變得快。但他強調這種變化是“特定的本土的變化”,而不是泛指的全球的變化。那種虛空的趨勢對他來說并沒有什么意義。
馬蒂賈特地在瑞典花費了幾個月時間,用來研究一個叫做“不穿衣的時尚”的新項目,他強烈地覺得時裝不只是時裝:“一種服裝本身就是一個建筑對象,并不是因為它的外觀、結構和紀念性,而是因為背后的想法。”但是外觀和結構畢竟是時裝背后想法的主要體現途徑,所以如何通過外觀、結構、肌理來體現時裝的社會屬性和空間關系,就成了時裝領域最難的問題。看似繞了一個大彎子,其實這些思維的曲折過程和馬蒂賈在服裝面料上的創新有很大關系。馬蒂賈說:“空間是服裝和建筑共有的語言,所以我經常借鑒建筑的設計方式,這就是我的項目為什么總是讓人先想看到’架構’的原因。”架構是他的面料呈現的驅動力。具體操作中,馬蒂賈是這樣做的:把對看不見的空間的癡迷用看得見的空間表達出來,應用到具體的服裝和面料設計上,則力圖通過小小的衣著之間(衣服、著衣的人,著衣的人與外部空間)的“建筑關系”和“建筑沖擊力”。
對空間的遐想和探索導致了馬蒂賈的衣服必須充滿空氣感,所以沒有一塊面料是死的。他的“結構情結”體現在服裝的肢端,就是將每一個他認為重要的部位和情緒延長出去:性感的前胸、躲藏的臉、語焉不詳的上半身——所有的衣服攜帶著人類情緒成為肢體表達的補充和延伸。這時候,材料最好能精確到立方厘米,好讓這種傳達更加細膩自如。但柔軟的纖維制品雖然足夠細膩自如,卻在廓形塑造上差強人意,不能滿足馬蒂賈對空間探索的明確欲望。所以他用了一種硬編織、軟雕塑的特殊方法來造型。在馬蒂賈這里,面料的位置不是前置的,而是后置的。傳統的因材制宜的方式再也不能滿足他了,設計師要根據自己最深層次的需求一步一步推理出所需要的面料,并用盡方法創造出這種材料,使創意精準落地。
3、煉金術士勞倫·鮑克的讀心術
相比之下,勞倫·鮑克 (Lauren Bowker) 似乎在面料創新上走得更遠,遠到甚至稱他的材料為“面料”都不知道合不合適了。勞倫·鮑克先后畢業于英國曼徹斯特藝術學院 (Manchester School of Art) 與倫敦皇家藝術學院 (Royal College of Art London)。 在校期間專攻紡織設計,研發了可變色鉻金屬墨水。這種墨水可以根據七種環境氣候指數的變化改變顏色,并吸收空氣中的污染物。在每一種具體情況下,墨水的表現都不同。“如果你告訴我一個具體愿望,比如你希望你的絲綢上衣在牛津街和貝克街時都呈現出不同顏色,我就可以走到你指定的地點采集環境參數,為你制造一款專屬墨水。”勞倫·鮑克自信地說。
由于可變色鉻金屬墨水可以用在印刷、噴涂,也可以用在纖維染色上,很快,許多領域各異的公司都找上門來尋求合作,他們顯然看到了這款材料重大而廣泛的商機。但勞倫對她的墨水卻有另外一幅愿景:“我希望將來它能用在醫療產業上,例如制造一款T恤給哮喘病人,每當哮喘發作時,T恤就會變色。這對我來說比擁有一個很棒的時裝系列更接近成功。“畢業后勞倫·鮑克帶領著一個由裁剪師、解剖學家、工程師、化學家組成的團隊,致力于研發可應用在穿戴上的高科技新型材料,追求著和哈利波特一樣的理想:知識創造魔法。勞倫的未見工作室( The Unseen)2014年在倫敦時裝周上發布了一組用新型面料做的衣服,這組面料能隨著來自外界環境的不同刺激,比如風吹、雨淋、摩擦、陽光照射甚至聲音的刺激而發生色彩上的奇妙變化。但這種不帶延伸應用的面料創新在勞倫看來還是較為傳統,事實上現在的勞倫·鮑克在可穿戴設備上的“面料設計”領域,也已經走得更遠。
說到可穿戴設備,更多人聯想到的是電子用品,雖然它聽起來完全是一個服裝行業的名詞。市面上的可穿戴設備幾乎沒有服裝領域的設計師介入,逐漸審美堪憂。勞倫·鮑克團隊的這款高科技頭套,也許是這兩者之間的橋梁。這款由4000多顆施華洛世奇黑水晶和可變色材料制成的頭套,核心材質本身與人類的骨骼十分相似,與人體貼合嚴密;外觀上的這些材料在吸收了頭部點熱量損失后會發生顏色變化,通過黑橙紅綠藍紫的顏色變化來反映大腦活動和人類情緒,當思維有劇烈動蕩時,頭套的色彩變幻莫測。這種設計很顯然已經屬于生物學、化學與藝術設計的交叉學科,比交互設計多了服裝領域的特征,又從服裝材料領域延伸到可穿戴設備領域分了一杯羹。
勞倫解釋道,這款頭飾之所以能根據思維變色,是因為外界環境釋放的信息素發生變化時,人的神經元就會被激發并發生改變。所以根據人對信息素的釋放情況,頭飾上的水晶便能夠通過化學物質的混合發生顏色的改變。“我感興趣的是那些看不到的變化。當外界的環境或信息素發生變化后,人體所釋放的信息也不盡相同。由于這種信息素釋放的變化,頭飾以及一系列該類型服飾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除了馬蒂賈·科普、勞倫·鮑克,還有一位丹麥設計師安妮·索菲·馬德森 (Anne Sofie Madsen) 也在面料創新上頗具特色。她的創作風格奇異瘋狂,手工細節錯綜復雜,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畫風”很詭譎。但是與前兩位比起來,安妮·索菲·馬德森用的材料卻平平無奇。她的改造沒有太多大刀闊斧的動作,主要還是遵循基本原理,在已有面料的基礎上使用褶皺、手繪、鏤空、折疊等傳統方法對服裝進行一種拿捏很準的整體氣氛調試。視角相對柔美許多。但是這樣”畫出來“的面料改造,也十分令人難忘。
這些百花齊放的年輕實驗者,將面料與各門類學科之間的諸多隔閡打通,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多維空間。他們之間的差異性很大,卻無一例外不是從“借調”的角度參與到面料設計當中。他們以“偷語”、“偷意”、“偷勢”的方式,以不同初衷和身份成為一個“面料設計師”。這是當前面料設計大變之下的現狀。這種現象的優勢在于背景的多樣化帶來的可能性,劣勢也在此。
每一個交叉學科的風暴中心都面臨著開放平臺帶來的好與壞,如今看來,對于面料設計來說,能否在開放之后迎來一個新的學科凝結,可能也只能交給時代和時間了。但正如約翰斯頓所說,“沒有面料,就沒有時尚。”面料設計這個服裝設計金字塔尖的部分,也是時候為大眾所知了。